
描述爱尔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经历有多种方式。你可以聚焦于政治文化上的异同——这些差异与共性本身就充满魅力。那些交织与分离的历史轨迹。你也可以着重分析这里的就业市场,以及吸引爱尔兰人远离故土、奔赴地球另一端追求新生活的拉力因素。
当我在此类话题上撰文时,部分读者并不热衷。我曾收到一封邮件,对方从本体论角度为利特里姆郡的地域价值与概念意义辩护,通篇夹杂着激烈的咒骂。只因我曾调侃这个郡与我的故乡利默里克一样,对年轻人而言缺乏悉尼那样的吸引力。
你也可以探讨爱尔兰与澳大利亚外交经济关系对爱尔兰的重要性。我偶尔也会涉及此类话题,尤其曾在一篇专栏中伪装成《爱尔兰时报》专栏作家兼奥威尔奖得主芬坦·奥图尔,混入爱尔兰使馆的圣帕特里克节庆典——事实上我整篇文章都在剖析爱尔兰人对"now"这个词的妙用,只因有位女士抱怨这种用法让爱尔兰人显得不够严谨。此刻为您呈现。
辟谣本身就能轻松写就数版篇幅,我也确实这么做过,因为爱尔兰人对澳大利亚始终存在某些误解。这些臆想既包含过度乐观的憧憬——比如认为所有人都毗邻温暖的金色海域且个个相貌出众,也掺杂着略带贬义的评判——比如认为蜘蛛无处不在,每年大白鲨会咬掉一千四百万居民近七百万条腿,或者每顿饭都是早午餐。最后这点近乎属实,但又不尽然。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真相而非现实写照。不过下一届政府会带来何种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即便对那些有幸拥有选择权的人而言,移民仍是复杂的抉择。移居澳大利亚意味着对故土可能性的告别,是刻意脱离家庭生活与朋友圈的清醒选择,这种选择让你在实际层面脱离了这些关系网中的日常欢愉与责任。
不会有人因抢到绿洲乐队门票而请你照看孩子,不会邀你参加生日派对,不会将你纳入每年家庭海滩旅行名单。当他们陷入困境、情绪低落或需要帮助时,你不再是首选求助对象。无论诞生或逝去,你始终隔着超过三十小时的物理距离。这段时空鸿沟无法逾越。当事情具有时效性时,你必然被排除在外——或许无法及时赶回,甚至根本无法返回。所有体验都带有延迟性,这种延迟造就的隔阂远超物理层面。当你选择离开,就必须接受故土生活仍在继续的现实,无论你的心绪有多少仍系于彼方。
移民经历中最令我着迷的始终是这些日常细节。那些构成生活的微小瞬间,需要权衡、接纳与背负的得失损益。澳大利亚城市布局与都柏林、科克或高威那些你烂熟于心的街道产生的强烈疏离感。更换早餐麦片品牌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竟会带来细微的背叛感或苍白的妥协感。每个清晨窗外异域野生动物的喧闹虽生机勃勃却催生孤寂(我怀念肥硕木鸽"谁?谁?"的探询鸣叫,但也获得了华丽凤头鹦鹉如翼龙般的尖啸)。问候语的变化——澳大利亚人用"How are you going?"替代我们的"How"s it going?"或"How are you doing?"——能同时激起诡异的熟悉感与陌生感。
通过书写日常中那些让移民生活既甜蜜又艰辛的细微之处,我得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在澳大利亚这种既截然不同又莫名相似的生活。这正是打包人生移居世界另一端的真谛——这里既有文化冲突、民族认同传承、经济适应等重大命题,也有深更半夜躺在钴蓝色的黑暗里,听着城市工人莫名在凌晨时分用吹叶机清扫街道,感受那些永远无法理解的微妙差异。这些奇特琐碎的事物,会让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
本专栏读者不时来信,有人认为我对爱尔兰过于消极对澳大利亚过于美化,也有人持完全相反观点。有位女士曾来信建议我避开爱尔兰身份认同的棘手问题,只写人们爱看的海滩题材。我住在内陆城市堪培拉。当我应要求写了篇邦迪海滩游记(其实有些名过其实),有位男士愤然来信指出克莱尔郡的西班牙角沙滩毫不逊色,而且肯定更少鲨鱼袭击风险。
本周有位女士对上一期专栏极为不满,那篇探讨了细微无形的文化差异如何时刻提醒移民身份的文章。她认为缺乏思想深度。但所有移民都明白,随波逐流往往行不通。当你脱离原生文化环境,就不得不持续解析、比对、审视周遭世界。无论我在悉尼疯狂寻找香料包,还是思考远离故土后爱尔兰特质如何演变,这些都是思想层面的探索。至少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你无法取悦所有人。
或许芬坦·奥图尔会把他的奥威尔奖借给我。
- 注册《爱尔兰时报》海外通讯,获取全球爱尔兰裔相关资讯。我们将为您呈现海外读者的生活故事,以及与世界各地爱尔兰人相关的新闻、商业、体育、观点、文化和生活报道
- 若您旅居海外并愿分享经历,请通过下方表格或致信abroad@irishtimes.com,附上简要个人信息。感谢您的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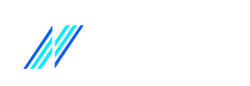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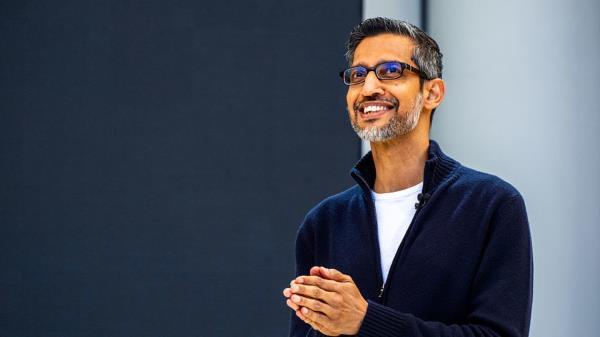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