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说,曾经存在过一种叫做"单一文化"的东西,如今它已彻底成为历史。在当时我们并不这样称呼它,因为我们正身处其中,就像谚语中的鱼不需要专门为水创造词汇一样。这里我特指的是流行文化而非更广义的文化(尽管后者近年来也出现了多重深刻裂痕)。单一文化意味着无论你是否喜欢《老友记》,都能哼出它的主题曲;当你和所有认识的人都至少看过一集《德州巡警》或《恋爱时代》,那就是单一文化;当你被迫熟悉Ace of Base、仙妮亚·唐恩、西城男孩和B*Witched的音乐——因为除非采取极端生活方式,否则这些旋律总会无孔不入地钻进你的耳朵。
并非说单一文化全然糟糕:神奇的是,它也曾让小学全班同学都追看前夜的《双峰镇》剧情,让涅槃乐队《In Utero》这样阴郁另类的作品奇迹般席卷主流乐坛。那些与主流文化激烈冲突的事物,反而时常因其反叛特质突破重围,成为全民焦点。
很难精准定位单一文化的消亡日期。当《权力的游戏》2019年完结时,许多文化评论家宣称"万人同步追剧时代"就此终结。但我更倾向于将终点定在五年前——作为专栏作家,我需要一个足够抓眼的论断——我认为它在2014年9月9日星期二正式死亡。那天苹果iTunes用户一觉醒来,发现U2新专辑《Songs of Innocence》被强制塞进曲库,人们愤怒地要求将这个"礼物"扔回虚无。
这个时刻之所以令人玩味,之所以被视为单一文化的最后哀鸣,是因为承载U2专辑的在线音乐平台本身,正是确保文化产品不再被共同拥有的信息技术典范。
iTunes及其后继者Apple Music、Spotify、Tidal等的核心逻辑,是让每个人随时获取所欲所求,开启高度个人化的音乐旅程。理论认为,互联网——连同其音乐流媒体、视频分享网站、社交媒体应用和永不停歇的内容喷涌——杀死了单一文化。被迫接受文化产品灌输的日子结束了。U2自诩前卫的技术操作,在这个即将被迷因和微趋势淹没的世界里,反而成了错位的复古行为。
最近绿洲乐队重组巡演的事件,让我重新思考这一切。它仿佛短暂重现了旧文化秩序——如果你看到这里心想"实在不想再读绿洲重组新闻",那恰恰印证我的观点。这几周每次翻开报纸、刷Instagram或听到电台,加拉格尔兄弟复出的消息都会扑面而来。
当克罗克公园演唱会期间绿洲相关内容霸屏时,我的Instagram突然弹出An Post邮政广告:一个穿着连姆·加拉格尔标志性派克大衣的绿色邮筒卡通形象,唱着"因为也许你会是那个寄信给我的人"——生硬改编自《Wonderwall》的副歌。营销人员显然庆幸终于有个全民文化事件作为宣传支点。
或许我对这个临时蹭热度的广告过度解读了,但它确实诡异重现了前互联网时代的单一文化体验:当所有人拥有共同文化坐标,生活在大致统一的文化语境中。至少对我而言,这种怀旧并不美好。它令人莫名沮丧,让我意识到尽管偶尔沉溺 nostalgia,我其实并不真正怀念那个旧时代。
但如今人人盯着手机获取不同内容——所有人困在各自固化的个性化信息茧房——并不意味着主导文化已然消失。这些技术手段:手机、占据我们清醒时长的各种平台,以及日益成为媒介化世界核心的AI软件,正构成新型单一文化。我们在其中获得的表面是个性化体验,深层却是顽固的统一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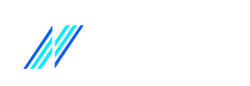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