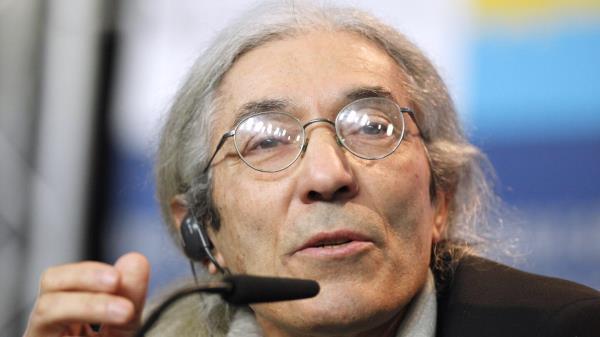为什么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需要而不是减少艺术与人文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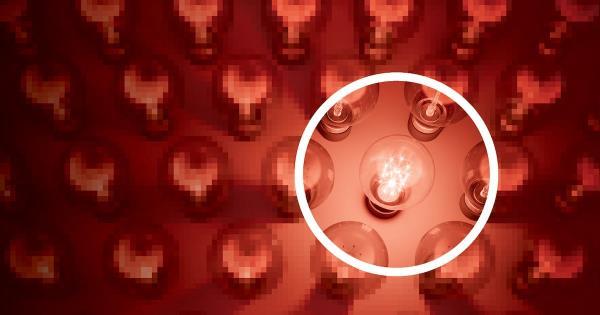
在现代经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执行力"是王道。人们常说创意很廉价——谁都能想出来。
真正重要的是执行能力:建设、扩展、分发的能力。更关键的是,执行成本高昂,因此催生了一整套旨在提高执行效率的科学与管理研究领域。投资者寻找的是能实干而非空想的创业者。社会建立的机构旨在培养实干家,而非梦想家。
但这个时代正在终结。
在"智能体AI"与自动化机器的时代,执行力不再是稀缺资源。如今机器可以编写代码、起草商业计划、设计用户界面、创作艺术甚至谈判合同。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完成的任务,现在只需一人一电脑就能搞定。
初创企业创始人不再需要会编程的联合创始人。艺术家不再需要平面设计师。建筑师不再需要制图员。他们需要的——也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是能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创意。
在这个新图景中,瓶颈已经转移。执行力变得充裕、商品化且近乎即时可得。真正的稀缺资源变成了构思能力:想象新颖、有意义且差异化事物的能力。这种思维较少源自STEM学科,更多来自艺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创意并非自然存在。它们无法通过逻辑或实验发现。创意是被创造的——通过隐喻、故事、类比、反讽、批判和语境塑造而成。它们在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设计与音乐中培育。在转化为逻辑与公式之前,它们汲取文化原型与人类经验。
STEM学科固然重要,但它们的功能不同——是检验创意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科学与技术建立在我们的创意之上。工程学应用这些创意。数学校准这些创意。这些都是关于精确性、证明与性能的学科。但发现问题的顿悟时刻、构想新用途的灵感,或是从意外角度观察系统的眼光——这些火花源自其他领域。
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不仅培养人的分析能力,更训练解释、重构与情境化的能力。在机器快速承担执行负担的世界里,正是这些能力将创造真正的差异。
尽管这些学科日益重要,全球高校却在重新分配资源,削减创意学科的投入。例如在英国,人文学科入学率持续下降:从1961-62学年的28%降至2019-20学年的仅8%。相关院系正在关闭。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报告显示,2012至2022年间人文学士学位授予量下降24%,二十多年来首次跌破20万。英语、历史等传统学科衰退尤为严重。英语专业人数较1990年代末暴跌约半数,历史专业较2007年峰值下降45%。
人文学科衰落不仅限于英语国家。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年人文学科学生减少22%,占大学生比例从17%萎缩至2023年的10%,主因是社会对STEM与健康科学的推崇。
法国作为传统人文学科重镇(约21%本科生修读艺术人文),也面临严峻挑战——当这些学科在精英学术界外的职业路径中显得愈发"无用",维持学习兴趣变得困难。
这是战略误判,是对21世纪价值迁移的误读。其根源是粗陋的功利主义逻辑——认为直接适用的知识才有价值。但在AI时代,应用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而构思(即产生原创想法)正变得越来越难。
社会若持续低估创意学科投入,恐将丧失竞争优势。更准确地说,当执行效率普遍提升时,真正的差异将取决于创意的质量、相关性与原创性。
艺术与人文学科并非全无希望。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意大利和瑞典的艺术人文毕业生占比超过20%。意大利尤为突出,22%毕业生专攻文学、哲学、历史或艺术。
这远高于许多欧洲国家(瑞士6%,荷兰7%),表明人文学科在意大利高等教育中仍占重要地位。这归功于意大利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教育体系对古典人文研究的重视。
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拥抱整个世界。"
为应对新时代需求,我们必须停止将人文学科视为奢侈品。它们不是装饰品,而是根基。它们是培养人们在变革世界中想象、叙事与重新诠释能力的学科。
政策制定者、高校与雇主必须相应调整投入。这意味着资助那些濒临关闭的院系,将艺术与社会理论融入AI与技术课程,培养善于提出更好问题——而非仅能快速给出答案——的人才。未来属于能创造意义而不仅是产出的人。
AI时代不是人类退场的时代——而是人类特有才能变得最重要的时代。
版权声明:本文由龙图网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